订阅
|
搜视网在线看最热影视 https://www.tvsou.org 侯孝贤、杨德昌的硬核粉丝观看完是枝裕和早期拍摄的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可能会略显失望。主因是内容较稀薄,时长只有47分钟。 《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1993) 这部于1993年播出的纪录片是富士电视台深夜栏目《NONFIX》的案子,它不是类似阿萨亚斯后来拍摄侯孝贤的那类「专业纪录片」,电视台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是为《戏梦人生》在日本的公映作宣传,所以必然有不少内容是普及性的入门常识,很多议题也没有深入的可能,硬核粉丝看来自然不会过瘾。即便如此,纪录片中呈现的那个年代侯、杨的人生状态,如今回看,还是挺叫人感慨。 可以先对比一些背景。如今已是金棕榈加持、享誉世界的国际大导演是枝裕和,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还没有拍摄过任何一部剧情长片。是枝裕和在1995年拍摄电影处女作《幻之光》之前,是电视台TV MAN UION的员工,主要工作是拍摄各种类型风格的纪录片。 《幻之光》(1995) 《幻之光》也是一部电视台制作的电影。所以长期以来是枝裕和一直把自己作为一名电视人。而之所以愿意接受富士电视台的委托拍摄这部纪录片,纯粹是因为拍摄对象侯孝贤的导师光环,以及他本人与台湾浓厚的亲缘性关联。是枝裕和的祖父母早年因为同姓的原因,无法在日本结婚,所以私奔日殖背景下的台湾,在高雄生下了是枝的父亲是枝兼藏。 是枝兼藏之后辗转流离于嘉仪、台南各地读书,二战爆发后被日本征召入伍,战败后又作为俘虏在西伯利亚劳改,一直到二战结束后三年才首次回到日本国土。这使得是枝兼藏一辈子与日本社会格格不入,却始终对台湾念念不忘。是枝裕和的童年时代,父亲每日家中念叨的永远是台湾的如何美好。 是枝裕和 侯孝贤之于是枝裕和是一种启蒙式的开悟引导,《幻之光》甚至是在侯孝贤的建议下特别申报威尼斯电影节,影片配乐人是《恋恋风尘》的配乐人陈明章(对《恋恋风尘》喜欢至疯魔的是枝在某次于东京与侯会面之时,强忍羞涩直接开口向侯导借用陈明章)。 而当《幻之光》拍摄完毕,侯孝贤看完后认为技术方面很好,但没有必要事先画分镜头,而是应该在现场跟随演员状态调整镜头。是枝裕和听完如五雷轰顶,羞愧难言。 《幻之光》(1995) 在无数的访谈中,只要一谈到侯孝贤,是枝裕和即刻就会动情流露出父亲般的仰慕之情,前几年为了去台湾给侯颁奖,他甚至甘愿自我隔离十四天,甚至表示隔离一个月都可以,而在隔离期间他又把侯的所有作品都拿出来看了一遍。 就具体作品来说,是《童年往事》(影片的第一个画面就是高雄县政府宿舍字样,这是是枝父亲魂牵梦绕的故土),让是枝裕和意识找到了家庭-社会-历史层面的联动表达方式。处女作《幻之光》初看,几乎是一部完全临摹侯孝贤的电影——固定静止画面,远景-长镜头,镜框内部的精妙构图,疏离的情感。 影片刚开场祖母走失要回故乡的那场戏几乎就是照抄了《童年往事》里祖母要回大陆的情节。 但仔细揣摩又会发现,其中有着是枝本人迥异于侯的表达,相较于侯倾力于捕捉人在自然时空流动情境中的怡然自洽状态,是枝专注于个体的情感如何在一个广大的时空中显现出来。《幻之光》是一部将个体内部深层次的情绪通过银幕空间扩散出来的冥思电影。 《童年往事》(1985) 有了这样一种师徒、父子之间联动关系,是枝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激动之情不在话下。 是枝裕和与杨德昌没有直接的交谊,他作品的母题、风格也与杨德昌相差甚远,但二人在某些观念上其实非常接近。 是枝早年有大量纪录片的拍摄经验,对纪录片他自己有一套立论,「我通过纪录片讲述的大多是事物中关于公共领域的部分,因此不管批判哪个方面,不管批判谁,最后都不会停留在个人攻击。我重视的是解读催生出这样的人的社会结构,从而展现出的宽度和深度」。 这个思路和杨德昌电影有着高度的同质性,杨德昌电影最关注的就是台湾社会结构中深层次的矛盾与困境,《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本省-外省冲突中孕育着台湾社会的改良可能,这种角度只有杨德昌才能观察到。 是枝裕和在访谈中也有谈到过杨德昌,他认为通常创作者的创作巅峰时段都不长,而杨德昌在完成《恐怖分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后,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居然还能拍出《一一》这样的杰作,很叫人佩服。 《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1993) 回到纪录片。在拍摄这部纪录片之时,侯孝贤与杨德昌正处于创作的巅峰阶段。二人当时最新的作品《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犹如两枚重型深水炸弹,浸透到台湾历史最幽深的黑暗之地,让人感受到亚洲电影前所未有巨大的历史穿透力。 可能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是枝裕和使用了历史的主题来作结构与脉络,展现出侯杨迥然不同的创作方法以及这种方法的由来。 影片一上来就是侯孝贤携李天禄参加《戏梦人生》日本记者招待会的场面,这个过程中,侯孝贤就谈到了历史,为何要拍摄《戏梦人生》,以及1895年到1945这段历史的被遗忘。可谓率先点题。接着就是杨德昌出场,在《独立时代》的片场,他介绍了一些影片的拍摄情况。整部纪录片的结构差不多就是如此,轮流拍摄二人,中间穿插了两个有关台湾历史、影史的场景。一是露天电影院的拍摄,二是红楼剧场的一些情况。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局外人,作为一部面对日本观众的作品,是枝裕和并不避讳侯杨二人的关系,直接以旁白的方式交代二人关系近来的疏远,这如果在华人导演拍摄的纪录片里面应该不会如此直白。 纪录片中关于侯杨的大量信息,虽然资深影痴耳熟能详,但直观的影像洞见如今来看还是颇为珍贵。尤其是枝裕和以轮番登场比照的方式拍摄侯杨二人,这种反差更为明显。 侯孝贤最为着力的,是传统社会里中国人的状态与气息,在纪录片结尾部分他的原话是说,「想用新的语言与形式来拍摄我感受到的中华民族的事情」。 譬如让他着迷的布袋戏大师李天禄,即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活化石一般的传统中国个体在世为人的存在方式,一种中庸的哲学,一种「人情与义理」的极限平衡术,再后来《海上花》里的洪善卿也是典型个案。 在台北都会区长大,接受了现代美国文化洗礼的杨德昌,则精英意识浓厚,一直以批判的知识分子眼光来审视传统中国社会的问题种种,各种结构性的缺陷,各种在现代性文明冲击下的挣扎、阵痛与创伤。 在纪录片里他谈到《独立时代》时,就表达了儒教文化背景下,独立自主的困难。这也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所隐含的一个深层次议题,一种文化与文明的现代性悲剧。 两个对比场景尤其明显,一边厢是侯孝贤娴熟地把玩传统泡茶技艺,另一边厢是穿着美式夹克的杨德昌在工作室的歌剧背景声中,看英文报纸,用电脑工作。 二人在拍摄现场的工作方式也有很大区别。杨德昌非常强调二元对立冲突性的场景,对演员情绪的掌控非常精确,分毫不差。侯孝贤则是醉心于现场气氛的把握,讲究光线的捕捉,人与光影流动的情境互动。而演员的表现一切以绝对自然的状态为标准,反复拍摄的目的是等待最合适的时光气氛。 有意思的是,侯孝贤片场的拍摄段落,再次反照出是枝裕和的迷弟本色。当时是侯孝贤在日本拍摄一则广告,广告内容是丈夫在听到妻子即将临盆的消息后在医院奔跑的场景。 整个场景的视觉构造和《悲情城市》医院里那场戏酷似,对侯孝贤电影如数家珍的是枝裕和果然应景地切到了《悲情城市》的医院戏,非但如此,他还特地拍摄了一个非常标准的侯孝贤式景框构图镜头,以示敬意。 纪录片中的两个历史场景,相对于侯杨的巨大身影,只能算是浮光掠影的点缀历史。街头放映的场景,篇幅比较短,用在收尾的时候算是象征历史的消散。 不过这段场景再次显出是枝裕和的迷弟心,因为街头放映中飘浮的画幅场景,正是来自《恋恋风尘》,这一点是枝在访谈时也毫不避讳的予以承认。 红楼剧院的篇幅相对多一些,这座诞生于1907年的剧院,可以归入中国早期电影放映的历史脉络中。剧院老板一口浓重浙江口音的蓝青官话,则是动荡飘浮离散的现代中国命运的绝好象征。 影片还特别拍摄了一段令大陆观众莞尔的史实,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台湾戏院在放映电影正片前都要播放仪式性歌曲,意识形态统合层面的灌输意志是如此顽强执着。 距离这部纪录片的播出已经过去近三十年,台湾电影的历史也已发生巨变,杨德昌作古已经十多年,侯孝贤最近十多年产量巨减,已到人生暮年。是枝裕和则从一位侯孝贤的迷弟,不断蜕变,调整风格,铸就全新自我。 新世纪以来,他的电影不断关注血缘-非血缘共同体命运以及个体在共同体中的丰富性感受,这在东亚儒教社会特别具有现代价值与意义,也是是枝裕和能够入列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当代日本导演的重要原因。 《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以吉光片羽见证了亚洲电影内部的美好联动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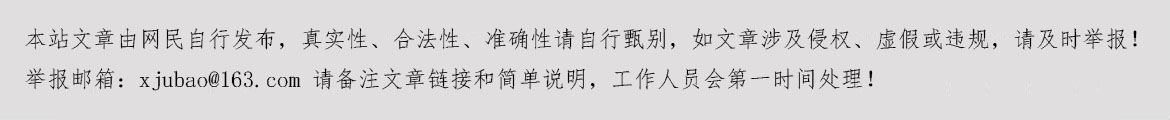
|
|
10 人收藏 |
 鲜花 |
 握手 |
 雷人 |
 路过 |
 鸡蛋 |
收藏
邀请